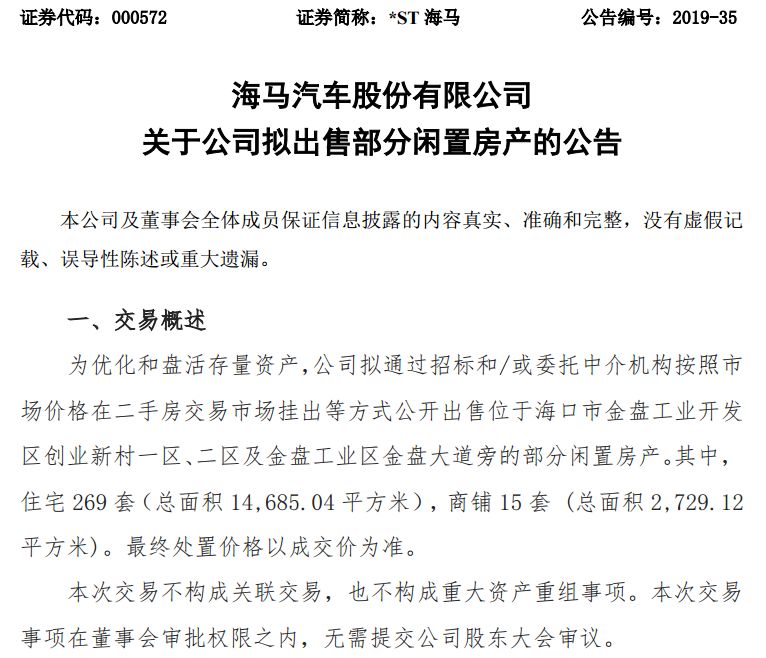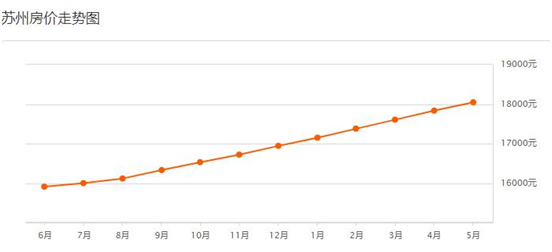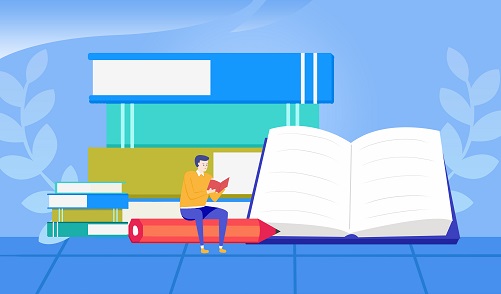人这一生,有些执念大概真是刻在骨子里的。于我而言,这执念,竟是想有一把“枪”。
这念想,来源于半个多世纪前我居住过的大杂院。那时节,日子是慢的,天地却大得很,孩子们能在屋前的空地上、过道的长廊里疯跑。最时髦的小孩,便是腰间别着一把乌黑的“手枪”,神气活现。院子里木匠张爷爷的刨花堆,是我们的宝山。我们这群“匪兵”,整日在那里扒拉,专挑那些纹理顺直、木质紧实的下脚料。找到一块巴掌大的木头,便是“手工制枪”的希望。
“枪”的诞生,是一场庄严而笨拙的仪式。先用小刀,费力地削出手枪的大概轮廓:枪管要直,握把要圆润,扳机处得小心地抠出一个月牙形的凹槽。这便耗去大半晌的工夫,手指常常被木刺扎得生疼,或是不小心划破一道小口子,也顾不上,只在嘴里吮一吮,又接着干。粗坯成了,便到了最精细也最磨人的阶段——用寻来的碎玻璃片,一下,一下,耐心地刮,直到刮去所有毛糙的棱角,直到那木头手枪表面泛起一层温润的光,仿佛有了生命。最后一道工序,是上色。我们没有漆,墨汁是唯一的“武器”。一方最廉价的墨块,在破碗底里兑上水,用毛笔尖蘸着,屏住呼吸,将那墨色一点一点染到木枪上。墨汁干得慢,一不小心,手上、脸上便蹭得东一道西一道,活像戏文里的小花脸。可我们不在意,只举着那沉甸甸的“乌枪”,迎着风,对着想象中的敌人,“啪!啪!”地喊着,心里那份满足与威武,便是给个金疙瘩也不换。
 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那把小小的木枪,是我童年英雄梦的全部寄托。夜里睡觉,也要将它压在枕头底下。有一次,院外小广场放露天电影《平原游击队》,看到李向阳双枪齐发,鬼子应声而倒,我激动得很,散场后一路狂奔回家,摸出枕下的木枪,在月光下比划了半宿。那墨汁的涩味,混着木头的清香,还有夏夜露水的气息,便这样渗透到我记忆的最深处。
后来,我按部就班地读书、工作,成了一个与枪械再无瓜葛的寻常人。只是偶尔,在新闻里看见阅兵式上整齐的方阵,或是影视剧中军人们挺拔的身影,心底那根沉寂已久的弦,会轻轻一颤。
不承想,这弦还有被重重拨响的一天。那是外出学习时,安排的军训中,竟有实弹射击的课目。去靶场的路上,我的脚步是稳的,手心却微微有些出汗。
靶场在山脚下,空旷,肃杀,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陌生的、严肃的气息。当那把54式手枪真正握在手里时,我愣住了。它和我想象的、和我童年摩挲过无数次的木块,完全不同。它是那样地冷,那样地沉,铁质的坚硬透过皮肤,直抵骨髓。一种陌生的、令人心悸的力量感,静静地蛰伏在它的线条里。木枪是温和的幻想,而这真铁,是沉默的法则。
轮到我了。打完手枪,再打95式自动步枪,我趴倒在步枪射击位上,脸颊贴上冰凉的枪托,世界忽然安静下来。远处的胸环靶,在准星里微微晃动。我深吸一口气,想起教官说的“有意瞄准,无意击发”,食指终于扣下扳机……
枪身猛地向后一撞,撞得我肩膀生疼。一股奇异的、带着焦糊味的青烟,从枪口袅袅升起。那一瞬间,整个身心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暴力美学所攫取、所震撼。原来,这才是“枪”!它不再是枕下的玩伴,它是一种决断,一种带着硝烟与后坐力的、沉甸甸的成年礼。
作者:魏琪
来源:扬子晚报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关键词: 最新资讯